

地址:潍坊市奎文区胜利东街246号
联系人:赵忠凡
联系电话:0536-8988111
手机:15653610519
邮箱:zhangzong@jwhj.net
邮编:261041
 微拍堂
微拍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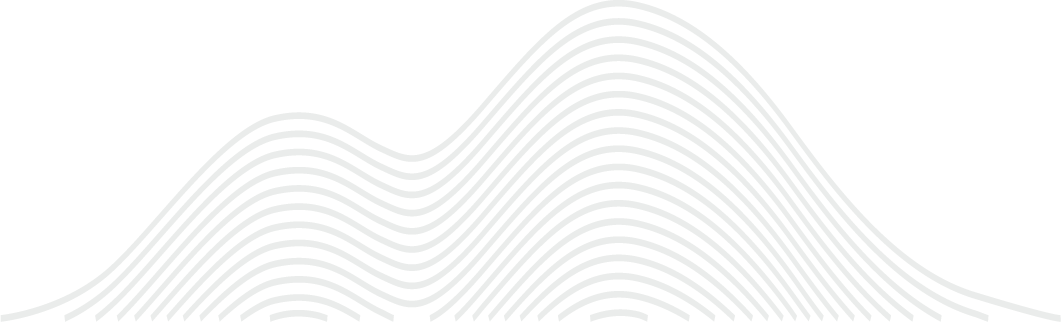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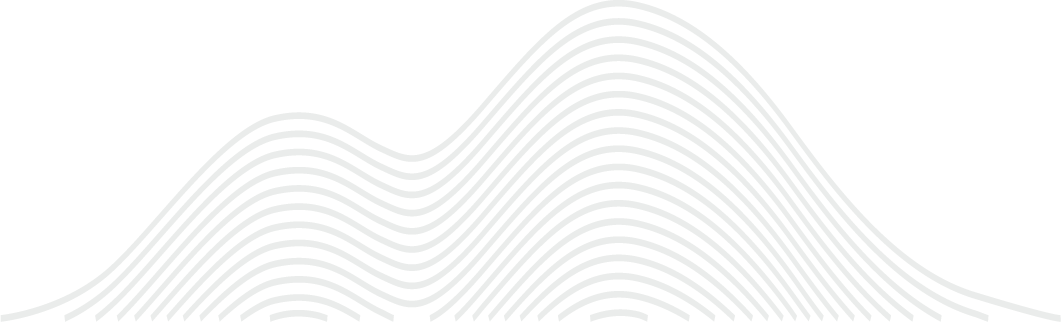
 2012-02-21
2012-02-21
 598
598

《阵地上有把吉他》
习惯了弹落石飞
拨弄着火红烟黑
潮湿的猫耳洞
没有让兴致变霉
绿色的年轻 拨动
跳跃的分贝
隆隆的炮声 恰似
振奋的沙锤
呼啸把和弦撕碎
那是进攻与固守派对
沉着不需要理会
听 硝烟浓重的混响里
歌声悠然陶醉
“啊 年轻的朋友们
愿我们自豪地举起杯
挺胸膛 笑扬眉
光荣属于八十年代新一辈”
那把吉他 来自
出发前家乡赠慰
仅有的技法 其实
阵地上刚刚学会
可《龙的传人》永远《我的中国心》
我为《我的祖国》献上《心中的玫瑰》
《当兵的历史》留下青春无悔
《我爱老山兰》芬芳了朝霞夕晖
想起梦中《妈妈的吻》
远方飘来《故乡的云》
于是《打靶归来》后
多了些《思念》 多了个《啊美 啊美》
《相思河畔》柔情似水
《在水一方》无花有泪
高山感赤诚而肃然
沙哑的低吟
安静了
雨林中高亢的画眉
阵地上的吉他
向英雄喝彩 为胜利举杯
阵地上的吉他
向战争诅咒 为和平万岁
《老山 月亮》
在老山
月亮是稀客
她和战士们一样
常常为阴湿的天气皱眉
皱眉那湿漉漉的风
留给被子的沉甸甸的记忆
还有记忆里那个湿透了的梦
而梦中的太阳还没有升起
铺板下 蘑菇已撑起了避雨的伞
远处
分明是一幅湿漉漉的水墨画
在画家笔下
挥洒淋漓的江南
月亮 应该是圆的吧
在老山
月亮可以去想像
一把土 有数不清的焦灼
却找不到一丝温馨
月亮
有时在战士的梦里光临
光临
父亲宽厚的眼神
母亲笑开的皱纹 以及
妻子攒了一年的热吻 还有
吻在儿子脸上的胡茬
而梦中的拥抱刚要温暖
撕裂夜空的轰鸣
也撕裂了 这虚妄的缠绵
那把吉他会拾起那个梦
他总是把《十五的月亮》
弹得那么圆
而战士们
总是那么静静地听着
擦着手中的枪
心中的月亮 擦的
又圆 又亮
.........
 |
 |
二十五年前,猫耳洞中的那段日子,又慢慢地显现在眼前。
一向喜欢独处的我,很少串门走动。友邻有两个同学,琴友兼棋友,也总是他们来找我。在连部实在凑不起手的时候,我偶尔应邀打打麻将。绝大部分时间,我都沉浸在一个人的世界里。
所谓猫耳洞,是用矩形钢构筑的工事。两米长,宽高各一米七,上面覆盖了两米厚的防弹土石,里面支一张床,加一个炮弹箱搭起的小桌,这已是几种式样中最宽大的一种,是上一任部队连长的寝卧,唯一的缺憾是不通电,白天夜晚烛光相伴,不过,我很知足。怀想之下,即兴一首:
《猫耳洞》
编织袋装满石土垒在洞口处
其余五面有矩形钢把我掩护
袒胸露腹上下只穿一条短裤
抹药黏糊但求蚊蝇不来散步
胶鞋对捂最怕蜈蚣食指般粗
床沿泥途应是老鼠不时出入
躺倒仰望角落蜘蛛来回忙碌
扭头看见枕边蜗牛打着招呼
伸手四壁雨水从缝隙里渗出
直身碰头坐在烛光下面读书
寂寞围堵可遐思任浪漫飞舞
的确非常想家似乎很少孤独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场中越战争,让“猫耳洞”成为那个时期的关键词。全国掀起的 “祖国在我心中,战士在我心中”活动,使得媒体对前线热切关注“猫耳洞” 这个军事上的战术名词,突然间传遍大江南北,一时家喻户晓。对那些有机会到前线访问报道、体验采风以及演出慰问的领导、媒体、艺术家来说,猫耳洞是个必去的地方。我在这方面条件得天独厚,借此,我接触到了很多艺术家。有彭丽媛、董文华、 铁源、士心等,他们都来过我的洞,并在我们的炮阵地上即兴演出。 印象深刻的是士心,他相声说的好,随和、热情、真挚。我还带领全排在他的导演下为他写的一首歌拍了录像外景。

诗人尚方也是在我猫耳洞里认识的。她被我的对联吸引,指导员领她来找我,在她和指导员的劝说下,我心怀忐忑地拿出了我那段时期的部分诗作。她肯定我的情趣和坚持,强调真情实感的重要性,留下她的联系地址,鼓励我多写多联系,并带走了我的两首诗。两个月后,我收到尚方寄来的最新一期《解放军生活》,我的《老山 月亮》 被她修改后取名《湿漉漉的记忆》刊登在杂志上,这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发表诗作。
那个时期,我最钟爱的是书法篆刻。画画虽从小喜欢,却不具备专业学习的条件,爱归爱,自信心不足。而诗对我来讲,更多是阅读上的兴趣。枕边诗集上前辈和才俊们的名字大山一样在我眼前矗立,我没有作诗人的妄念,写归写,从未敢投稿,只为一份心情。不过,一首小诗的偶然发表却让部队领导认为,我是可以写点东西的。部队从云南回到山东原驻地后,我被借调到师宣传队,任务是:歌词创作。

按说从战场到后方,在我的想像里应该是荣归故里,饮誉载功,再接再厉。但现实是:掩盖所有矛盾的大矛盾 ——“打仗”结束了,以前被掩盖的,加上一年来积累下来的所有矛盾,猛然间凸显,部队突然面临一场空前的看不见硝烟的精神考验。这方面,部队领导也估计不足,回到原驻地仅几个月,我的团发生了一系列让人震惊的事,我第一次领略了,那些荣誉编织的光环在人性面前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和不堪一击。战争不仅仅造就了职业光荣和人生骄傲,同时也在制造着伤害。这种伤害不仅来自敌方,也来自战争本身;不仅是肉体上,更严重、更长久的是心灵上。战争在我的概念里较之刚从军校毕业时已有了太多的改变,我第一次想到:我 是不是不适合做一名军人?我是不是应该离开?至少是离开我所在的部队。
这样的状态,我能写出什么样的歌词?起码是写不出符合部队领导要求的歌词。我非常无聊地在宣传队呆了两个月,浮躁茫然,毫无作为,决定休假。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三十六计走为上, 太多的问题是没有结论的,不如放下, 旧的结束, 新的就开始了。
八六年六月部队回到原营房,七月我借调师宣传队,九月休假,十一月如愿调离了原部队,我从一名炮阵地排长变成坦克八师二十九团政治处组织股青年干事。第二年,恋爱,结婚,我更加痴迷于书法篆刻,诗,不知不觉渐渐地淡忘了。
我爱人是除我之外唯一看过我那个笔记本的人,当时我们刚认识不久,我还很有些不好意思,甚至想把它付之一炬,可又有些不忍,便把它存放在箱子里了。二十多年,几经展转,没再打开过。若不是这次文章需要,它可能还存放在那里。今天重温,我仿佛从远处看到了我的年轻,心跳耳热之余,我很有点为自己的青春感动。